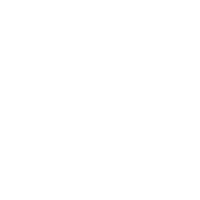建立電子資料庫搶救瀕危語言
隨著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的發展,國際語言學界最近也展開了一場科技革命,打算利用科技來「搶救」地球上日漸稀少的語言種類。而這大概也是為甚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月前聯同美國國家人道贊助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共同贊助設立了「瀕危語言電子超結構數據庫計劃」(Electronic Meta-structur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 Data Project)的原因吧!應邀出任該會顧問之一的城大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副教授、藏緬語實地調查先驅羅仁地博士對此表示:「近年來,國際語言學界愈來愈意識到『瀕危語言』研究的迫切*。建立一個『超結構』的資料庫,可以讓大家通過標準方式快速索取所需資料,共享電子數據庫的資源,這對『瀕危語言』的研究和了解會有很大的幫助!」此外,羅博士也應邀參加了日本教育部(文部省)贊助的大規模「亞太地區瀕危語言研究計劃」(Project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Rim)。
重視實地調查
也許是受到加州大學(柏克萊)重視實地調查傳統的影響,早在1983年羅博士還在修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就發展了這方面的興趣,並且對此情有獨鍾。羅博士說:「我對所有跟語言有關的東西都很感興趣,如歷史、文化、物理、人體生理學等等。不過,我覺得最有挑戰*的,是去調查一個完全陌生的語言,那就好像在玩拼圖一樣,你必須給它拼出一個詳細的輪廓,並且學習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思考方式。」
雖然較早的調查經驗包括了在美國加州對當地的越南及柬埔寨移民進行語音調查,羅博士的興趣主要是在語支龐大而繁複的漢藏語系(包括漢語和藏緬語兩大語族)。他說:「藏緬語大約總共涵蓋了250到300種語言,其中有許多完全沒有記錄,是所謂的『空白語言』,大部分更是『瀕危語言』。」因此,他更集中精力,專研漢藏語中屬藏緬語族的一些即將消失的「瀕危語言」,如羌語、獨龍語和日旺語等。
「藏緬語在國際語言學界上其實是比較不受重視的,因為研究這個語族的學者很少,資料有限,而且大部分說藏緬語的地區位處偏僻,政治也比較敏感,既不容易去,更不容易做出成績來。」以羅博士研究的這三個語言為倒,羌語的通行地區,主要是在中國四川北部的茂縣、黑水一帶;獨龍語族是在雲南省西北一帶(靠近緬甸和西藏);而日旺語則是在緬甸北部一帶。要到達這些地區必須跋山越嶺,況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外國人一般極難獲得批准到這些地方進行實地考察。所以羅博士雖然從1985年就開始多次申請到這些地方去做實地調查,但一直要等到1994年這些地方的政治比較開放後,才能真的成行。
為瀕危語言建立資料庫
目前,羅博士正在快馬加鞭地為Rawang Text with Grammatical Analysis和Rawang-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進行最後校對。這是他在緬甸調查日旺語多年的結果。他同時也正在建立日旺語、獨龍語和阿儂語的網上方言地圖和語料庫的網站,該網站將來還會刊載各個語言不同方言的語音系統、語法系統、文化特徵、語言使用情況、照片、錄像資料和學術文章等等。
去年,當羅博士完成A Grammarof the Qiang Language with Annotated Textsand Glossary 一書後,本來想就此打住,停止對它的研究,把精力轉回日旺語和獨龍語上。不過,當他去年再度跋山涉水、舟車勞頓地到阿壩州藏族、羌族自治州進行最後一次調查時,他卻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科技文明對少數民族語言的侵襲,而醒覺到自己應該繼續為這些語言多做一點事。
羌族分佈的地區極廣,一座山只有一個寨子,而每一個寨子只有大約30戶左右的人家,由於聚居極不集中,所以很容易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羅博士說:「94年我開始到那裡的時候,只有近大馬路邊的寨子才轉說漢語。這些年來,愈來愈多的寨子通了電,幾乎家家都有電視,連我進行調查的那個高高地掛在山巔上的孤寂小寨也都有電視看了。加上很多羌人為了改善生活,都搬到平地居住。在這些外來因素的影響下,我覺得他們會很快地失去自己的族語。」
這個體悟,不僅使他放棄原來想暫停的計劃,更促使他決定向研究資助局和城大申請資助,展開一個大型調查計劃。他希望能夠利用三年的時間,對90個分佈於阿壩州藏族、羌族自治區的羌寨子展開大規模的調查。羅博士表示,這個計劃的目的是想在這些語言消失之前,給它們「照個相」,留下一點記錄。他也希望能透過互聯網,把這些辛苦搜集得來的資料,轉為人人可用、檢索容易的網上「方言地圖」。他說:「目前說羌語的大約還有八萬人口,在它變得支離破碎之前,我們除了可以給它留下一個比較完整的記錄外,還可以觀察一個語言怎麼樣在和其他語言接觸下逐漸消失的過程。如果等到年輕人根本都不會說了才來做,那就太遲了。」
同時鑽研語言學的理論研究
做為一個兼顧實地調查與理論研究、宏觀與微觀並重的語言學家,他深信類型學(typology)是一切語言學的根本基礎。他指出,語言學的範圍雖然很廣,不過,任何領域的研究幾乎都需要一個涵蓋面極廣的語言知識。「一個語言學家了解的語言越多,在進行語言分析時,才能比較知道該怎麼去分析,尤其是在進行語法理論的研究時,沒有類型學的基礎是根本無法做到的。」
當然,要對不同的語言有紮實的掌握,實地調查自是最佳的渠道。羅博士強調,一個語言學家,最好是能在進行理論研究之外,同時進行實地調查。他說:「去調查一個陌生的語言,難度是比較高,可是你卻會學到很多在其他方面學不到的東西。」